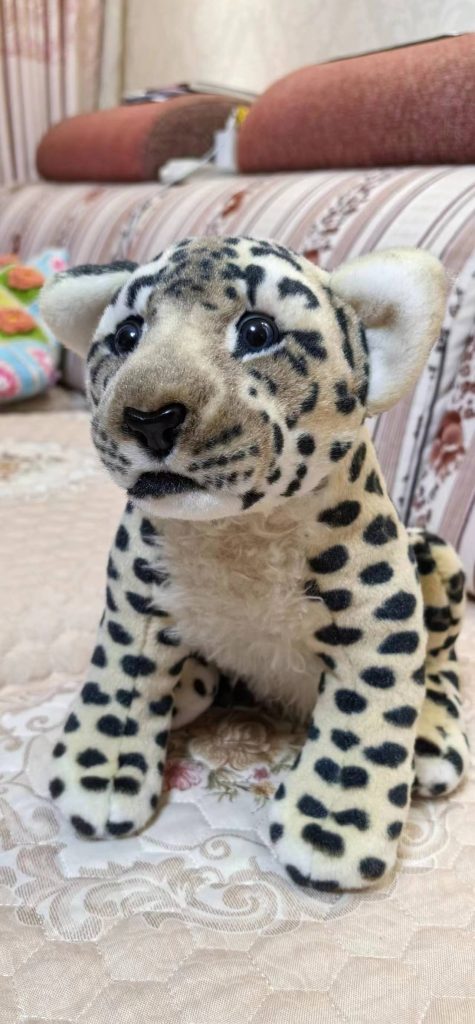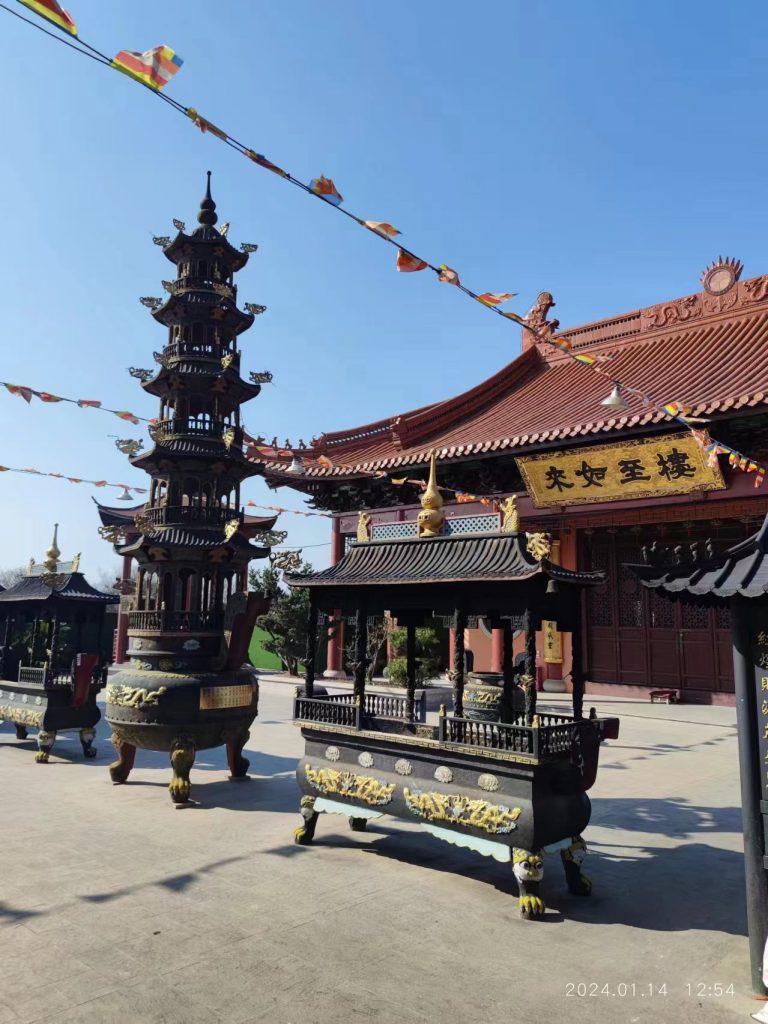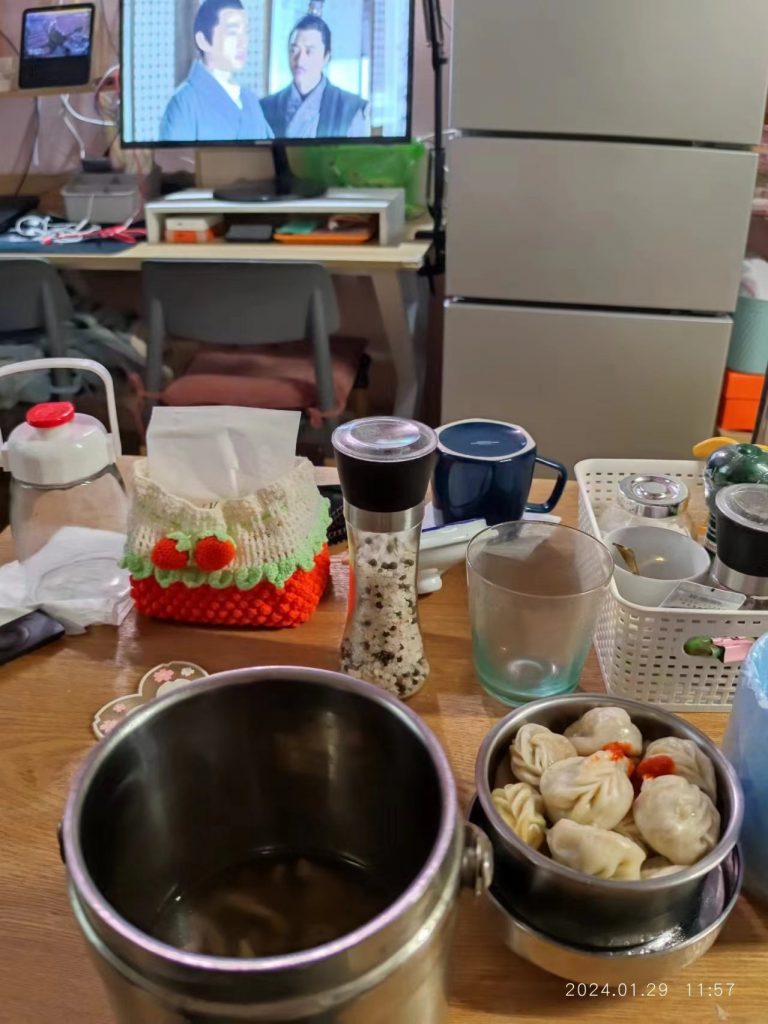春节结束,小姨一家顺利返程。
热闹结束,回归平静。




园区的花儿开了好些,微凉的空气里多了一些微妙的暖意。
护手霜刚好用完了,换成粉色的樱花款,味道非常淡,却十分应景。
这个味道,就仿佛整个人已经被某种即将温暖且欣欣向荣的氛围包裹着,很放松。
我对气味很敏感,一直都是,气味对我来说,包含着记忆、情绪和思想。
新冠之后,我的味觉迟钝了很多,以前对气味产生的丰富的层次感都消失了,只能堪堪分辨出香臭。
这种感官剥夺曾经一度让我非常惊慌,但是现在,我的嗅觉似乎在慢慢复苏,对气味又有了些分层的感觉,闻到以前用过的香水,或是带着过去气味的物品,我就会想起当时的心境——当然,或者是,我不知不觉习惯了现在这种“简陋的嗅觉”。
不过不管怎样,还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如此丰富的感触,说明我仍然很幸运,这就很好。




我也很喜欢这种平静的生活。
刚刚放弃了夕夕果园,用几斤玉米和一袋橙子忽悠老头老太太还可以。
想要控制老夫?你不配。
千言万语一句话,老子不稀罕。
为了“报复”并夕夕,特地去某宝某京上买了几样近期计划要买的东西,把并夕夕里对应的收藏和购物车删掉了——对,老子的格局就是这么小!
天音:你就不怕这是电商集团们串通好的路数么?
我:(ΩДΩ)……应该,还没这么智能吧……?
说起来,倒是很惊叹这种直接触发人类大脑底层的“精准控制”的方式,一遍一遍地强化结果,将你的目标锁定,然后,起初大刀阔斧神速进展,等到最后5克,开始出现的小数点后三位数的时候,我果断放弃了。
高明也是满高明的,激发了人的胜负欲和目标感之后,确实很难自己主动摆脱这种目标控制。
总有一种“目标即将达成投入了很多精力和成本现在放弃很不甘心”的“直觉”。
其实,换个思路想想,放弃了其实没有任何损失,最初引你上钩的“饵”,一箱橘子、几斤玉米,本来就不属于你,市价也不贵,你应该计算的是,十几块钱或者几块钱,能不能买到你的这些精力。
所以这种招数用来对付我,终究还是差了一口气。
我直接走你——,┏ (゜ω゜)=☞
说到这个,不得不佩服某音,这个抖是真的很强,随便点开,便无法自控,2、3个小时感觉一瞬间就过去了——仿佛是去了另一个次元,生活于另一种底层逻辑的世界。
明明只是看看短视频而已,却像是头号玩家的世界降临了一样。
某度、某B和其它很多类似的视频网站都做不到这一点,那些APP往往刷一会儿,刷到几个很反感的视频之后,就会想要关掉APP,而且,就算一直播的都是不太反感的,看多了也会觉得很腻歪,很快兴趣就掉没了,还是关掉干点别的事情去——但是某抖的神奇之处就在于,连刷3个小时,几乎不会出现任何你会反感的视频,就算有,直接划过几乎不会留下什么记忆点,而且,在刷的过程中,经常会对很多内容产生新的兴趣,于是再跟进几层,去搜索和探究,简直是绵绵不绝——真狠,这个算法,真是真绝了。
当然,也可能是某音的内容,每一条短视频都好像是一个“完整的碎片”,说“碎片”是因为它短,且内容的容量有限,但是说它“完整”,是它的短小中已经不知道为何把它的整个叙事背景说清楚了,不是额外说明或交代的,就是一直在那里的,在观看者心里,能懂,所以就是很神奇,后来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大概是某音的所有视频,虽然涉及领域和展现方式千差万别,但是,这海量短视频有一个共性,就是很“抖”,真的仔细看,每一条都是“抖里抖气”,就像是全频道的一分钟sketch大合集,刷的时候,看到具体视频之前,观众内心就已经有了这个“统一”的背景设定,所以每条视频不需要再自己多解释什么,直接开干就行,全是一个路子,唯一的区别就是有些拍得好点,有些质量次点——但是总之都是这路玩意儿,不会像其它刷视频网站一样,啥都有,是真的“千差万别八竿子打不着”,看着看着就跑偏了,某音不会,因为它的所有内容都出奇地“同质”。
这样想想,我对某音的“不可抗力”似乎也克服了,以后刷某音可以比照刷剧的心态,就很容易拿的起放的下了。
我对游戏的抗性很高,大概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手残,o(╯□╰)o,虽然我对游戏的兴趣是很大的,但是除了我自己做魔兽争霸的地图虐电脑之外,什么游戏都玩不来,空当接龙和花打僵尸不算。
但是对于视频网站,某音是真的牛,所以连我自诩心智金刚无敌,也只能把某音装在某台一般不在我身边的手机上,增加自己刷某音的前置条件的门槛。
我随身的电子设备里都不装某音——想看也没法看,自己心情不好或有点抑郁的时候,冲上去连续笑个俩小时——嗯嗯,最大发挥某音最正面的作用,平时绝不让某音出现在我的日常生活序列里,除了读书之外,真的就只有某音能让我的时光瞬间消失一两个小时,乐在其中地沉浸于某个让我舒适的异世界,大写的牛逼~
o( ̄▽ ̄)d
我一直讨厌被大数据裹挟的感觉,非常讨厌。
我知道在这个时代,这件事不可避免。
但是我有我的应对方式,比如我有4个手机号,装在4部随身携带的手机里:
1)工作机;
2)游戏机;
3)购物机;
4)家庭机;
专机专用,绝无互通,每部手机的信息和通讯录完全不同,我自己办公、家庭、游戏社交、购物的微信号也都是完全分开的,我给所有的自己建了一个微信群还有QQ群,“吾即众生”。
没有任何一款APP的同一个账号,可以同时存在于这四部手机上,同时在2部手机上的都很少。
我不在乎大数据读取我,但是不能完全读取我。
所以这样,每个APP都只能读到我的一个层面,谁也无法看到我的全貌,是真正的“物理隔离”。
我还习惯写“日记”,准确地说是blog,我习惯自己独立思考,遣词造句,不去自然而然地引用“官方”和“权威”,我习惯自己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是一直复述曾经呈现在我的视野里的“内容”,不管是推来的文章还是亲友的“朋友圈”,我要很久很久才会去看一次。
看新闻习惯性不看评论,对“带节奏”的说法和观点“本能”地“杠精附体”,就是不管看到谁说什么都会在思想里第一时间本能地“battle”一下,简单地说,就是把“质疑一切”训练成本能,深入骨髓地随时随地践行。
但是我不会真的去评论区回复找茬儿,我只是为了防止自己被大数据推送的信息裹挟,而不得不把自己的思想训练成“巴甫洛夫的疯狗”——逮谁咬谁,管他对不对管他是谁,先咬了再说。
无论他展示的观点是什么,我都先咬为敬。
没办法,我总要确定我还是我,才能向前走,才能确保是“我”走到了未来,而不是某具被大数据牵引的傀儡去了未来。
我写日记的习惯从小学开始。
三十多年了,除了纸质日记形式变成blog,篇幅可以更长,书写更便利,随时随地更方便记录保存,图像声音录像形式更加丰富以外,没有间断,没有不同,都是我最真实的“想法”,有些内容可能为了不被我言语间涉及到的相关本尊看到引起什么误会而有意“语焉不详”,但是我日志本质从未改变,它们就是最真实的——“我”。
我甚至怀疑要是有什么AI智能大模型看了我一生的“日记”,没准当场就会“立地成人”——
也是笑不活了。
人类一生多半劳苦蒙昧,有时要劈开众生和外部的一切环境,甚至,要劈开“自己”——才能真切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内核”。
而这个“内核”,又十分脆弱,容易被不相干的事物惊扰,被看似言之凿凿的屁话裹挟——不让自己被一切身外之物牵引控制,这很重要。
我写日志的习惯,仿佛是每天或者说每隔几天,我就有一次系统的独立思考过程,这种感觉非常好,很奇妙,虽然写的都是流水账,但产生的乐趣仅次于创作。
仿佛每次写日志,都把自己内心某种强大又真实的秩序夯实、强化了一点点。
可以真正坚定地贯彻自己的人生方向,既能从容地接纳他人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又能贯彻自己的想法,绝不动摇,这与某种一念执着的偏执,有很大区别。
我很喜欢这样的状态。

下班开车时看到的夕阳,我觉得它很美,是的,是我觉得它很美,不是我听说。